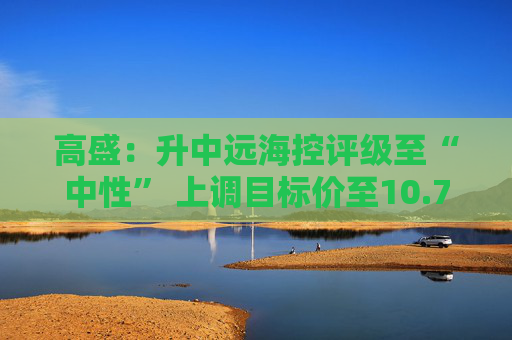刘乃菁 陈亮评《一词一宇宙》丨只有“人”才能理解语言
- 每日科技
- 2024-09-24 13:37:22
-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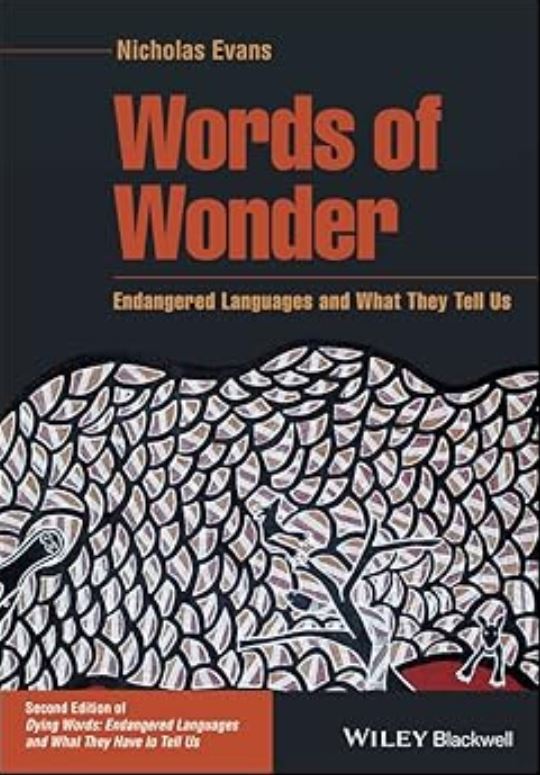
Words of Wonder: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What They Tell Us, 2nd Edition. Nicholas Evans. June 2022. Wiley-Blackwell. 320 pages. USD 56.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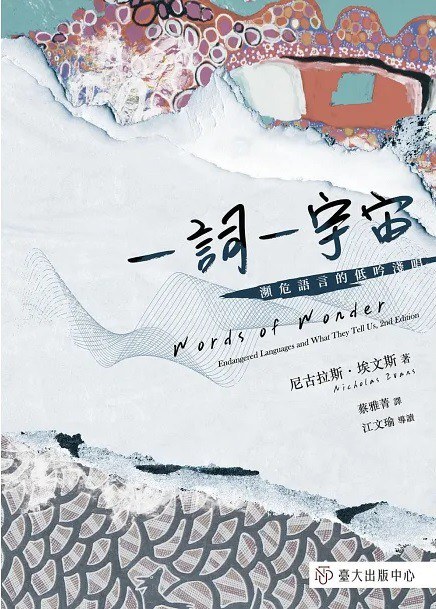
《一词一宇宙:濒危语言的低吟浅唱》,尼古拉斯·埃文斯著,蔡雅菁译,台大出版中心2023年8月出版
我们生活的星球上有七千多种语言,每种语言都像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与历史。我们通过学习多门外语至多能了解世界语言图谱中很小的一部分。不过,有这样一本奇书,可以将庞杂繁复的语言世界浓缩于三百页中。此书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尼古拉斯·埃文斯(Nicholas Evans)教授,也是澳洲人文科学院、澳洲社会科学院及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他以一本Words of Wonder凝结了数十载的专业研究和思考。一书在手,读者仿佛随着一位有经验的向导兼博物学家,乘坐热气球欣赏这个奇幻斑斓的语言星球,将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分布、源流一览无余。隔日,又随他在高山阔谷、平原森林中探索,与各种奇妙的语言邂逅,像博物学家采集动植物标本一样,收集并分析上百种语言的片段。夜晚降临时,这位“向导”在露营地燃起一堆篝火,向读者讲述学科渊源、奇闻逸事、点评每一个微小的发现背后的语言学理论。走出书中的世界,读者依然会不断回味这段令人兴奋而深刻的经历,同时对身边各种语言现象也有更立体的认识,提高对生活中语言现象的感受力与思考深度。
笔者试图从三个问题切入,介绍该书的核心议题。更“燃”的内容,还要请读者自己去一探究竟。
埃文斯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类语言为何多种多样?
巴别塔的寓言提到,人类最初只说一种语言,试图合力建造通天塔,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的僭越,便让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四散各地,无法合作。可是,这是人类语言多样的来源吗?埃文斯笔锋一转,引用经验研究,点明巴别塔只是带有神学意味的一种解释。尤其是小规模语言群落(speech community)的成员会认为,多种语言共存、各自说各自的语言未必是上帝的惩罚,反而有利于族群的利益。墨西哥的恰帕斯人(Chiapas)相传,人们曾经有段时间都学会了西班牙语,可以彼此理解。但随后各族和各城的人开始用西班牙语争吵,于是人们回到自己的小团体,只说自己的语言,才又恢复了和平。依据澳大利亚北领地的一个名为Warramurrungunji部族的口传历史,他们祖先从Croker岛去往内陆,沿途把生下的孩子放在各个地区,并告诉他们:“我把你放在这里,这就是你应该说的语言!这是你的语言!”所以生在不同的地方的孩子、他们繁衍的后代都必须说不同的语言。在澳大利亚北领地,一个人回到自己的部族的地方时,必须使用当地的语言,才能召唤出当地的精灵。换言之,语言是与人类繁衍生息的土地紧密联系的。地理和生计的多样,反映为语言的多样性。
以小规模语言群落的研究为支点,埃文斯教授探讨了语言多样性在社区层面的成因。澳大利亚的约克角(Cape York) 半岛,人们变着花样说话,把mawurr说成bawurr(his or her arm),去掉表示性别的鼻辅音“m”,讲自己的语言和邻居的语言区别开来。但人类一方面人为制造社区区隔,另一方面又通过多语制(multilingualism)打破这种区隔。通晓别的语言,会让个体拥有更多的亲戚、伴侣、社会地位。在非洲喀麦隆北部的Mandara山区,一个小伙子为了追求他喜欢的姑娘(来自Mada族),去之前列一个话题清单和Mada词汇表。在喀麦隆,孩子学习母语之外,在学校学习英语和法语,从老人讲述的故事中学习区域通用语Fulfulde,从邻村学习更多的语言。澳洲原住民穿越河流或部落边界,或者讲述祖先的史诗时,也会使用不同的语言。埃文斯教授在此回应了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言的两种语言发展的机制,一种是展现个体对于某种小团体的归属感,另一个则是与更广大的世界相沟通的愿望。读者可以借此对人类语言不断分化整合的动力学略有把握。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埃文斯教授又从人类社会进化史的角度,展开对语言多样性的讨论。这段论述首先点明,语言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大致相关。中文读者可以自豪地看到,在本土语言、本土语言谱系和本土高等脊椎动物物种三项指标上,中国均位居世界前列,本土语言数量(304)排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56)、印尼(390)、尼日利亚(480)、印度(390)、澳洲(353)之后。其次,从人类社会演化来看,狩猎采集社会是语言多样性的渊薮,而农业社会的兴起、大型中央集权政治的建立和帝国的扩张,都会吞并吸收这些小型的语言群落,压缩这种多样性。语言多样性的下降,自然引出了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性——语言凝结着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对周遭环境的经验认识,是人类的宝贵遗产。作者提到,西罗马帝国(27BC—476AD)兴起之前的意大利大概有十二至十五种独特的语言,随着罗马帝国的昌盛,日益被拉丁化。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世界范围内包括埃及、阿拉伯、波斯、马里、中国、朝鲜、印度、墨西哥、安第斯地区的帝国的兴起,多多少少都伴随着小语言的消亡。例如秦朝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然奠定了大一统基础,但对语言多样性未必是好消息。
小型社会的语言仍然在为当今世界作出积极的贡献——从参与世界大战的秘密通讯工作(如北美的纳瓦霍语Navajo),到打开自然界的丰富宝藏(如Seri语言),到发现能够对抗艾滋病毒的药物,无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语言的消亡速度却令人心痛——在本世纪内,世界上七千多种语言可能会消亡一半。埃文斯教授通过他自己学习研究卡亚迪德语(Kayardild)的经历告诉我们,学习语言并非只是掌握其语法,更要求学习者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世界。不过,会说卡亚迪德语的人已经日渐凋零。埃文斯教授在序言中写到,2003年,他参加了他的“挚友和大哥”查理·瓦尔达伽的葬礼,痛惜查理的后代和其它部落成员不能学习自己的语言所转达的完整部落知识,从此“不再能识别每一段海滩的地名、也不能用语言把乌龟哄出海面,更无法吟唱苍凉的史诗组歌”。强烈的人文关怀给埃文斯教授带来了一种绝望,也促使他动笔写下此书。
第二个问题是:语言到底是什么?如何研究语言?
世界语言多样性的消亡,为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也为语言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时代挑战。那么,古往今来,人们如何研究语言、保护语言呢?埃文斯教授带我们乘坐“时光机”,寻访古印度梵语文法学者以降保存语言的方式和动力。他提到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志和语言学巨著,是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修士的《新西班牙诸物志》(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堪称近代西方的语言学与民族志的奠基之作。但埃文斯教授也清醒地指出,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殖民扩张既留下了珍贵的民族志和语言学材料,也伴随着对当地文明文化的破坏。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晚期,德国莱布尼茨提出摒弃仅仅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这三门“神圣语言”的人文传统,提倡用科学方法研究当代所有语言,以了解人类整体。这种思想通过十九世纪的教育学家威廉·洪堡弘扬,变成“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显、需要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精神”的宏论,影响了一大批在战后前往北美的人类学、语言学学者。爱德华·萨丕尔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沃尔夫即是这一批人中的翘楚。人们的声音如何传达出我们的观念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语言科学的核心问题。
到底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提到语言-思维的关系,稍有人文背景的读者可能会马上联想到爱斯基摩人对雪的颜色的详细分类,以及语言/文化相对论。不过,这在埃文斯教授这里远远不够的。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是两种对立的理论——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理论和萨丕尔-沃尔夫开创的文化/语言相对论。他将两者置于公堂之上,通过对各种语言音位、词素、语法的“过堂传唤”,让读者领略到,普遍语法只在对有限的语言进行考察时有用;调查的语言越多,越没有办法验证语言具有普遍特征,而反例层出不穷。不同语言分音节的方式(Consonant-vowel或vowel-consonant)、在词层面上把世界现象“切分”成不同的范畴的方式、语法把语音和语义配对的方式,无一不挑战普遍性认知。反常的例子包括:亲属称谓可以是动词,英语和纳瓦霍语、阿祖格威语(Atsugewi)对动作的描述完全不同,纳瓦霍语的施受词缀反映着严格的生物层级,等等。当语言学工作者发现不同语言之间,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无法一一对应时,便不得不如埃文斯教授,承认“语言学比较像生命科学”,而语言模型似乎“更依赖于生物演化那种丰硕的创造性”。
这种基于大样本的语言研究产生对语言本体的深刻认识,仿佛把一支照亮语言研究的幽深路径的火把,交到了入门者的手上,引导我们细心琢磨任一语言中不可预测的差异与变化,更引导我们进入到单一语言的社会认知(第四章)。在此意义上,语法不再是厚厚的典籍的条目,而是不断地引导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关注、表达某方面的经验(同时忽略另一些经验)、协调行动的文化工具。换言之,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直达某个社会独特的心理特质。例如,英语中“我的椰子”所体现的所有权关系,在大洋洲语言中要强制性地讲明是供“我”吃果肉、喝果汁、还是长在土地上的椰子。英语中标志意图的“for”,在卡亚迪德语中可以细分成六类。英语可以表达他人的感受“他想喝水”,日语在描述他人意愿上则必须说“显得(如此)”“似乎(如此)”,在猜度他人动机上表现得相当保守。埃文斯教授更提出了语法中社会认知的一般模型,并用一个达拉邦语(Dalabon)句子Wekemarnûmolkûundokan来剖析语言如何精微地承载社会认知(读者一定会对这个例子留下深刻印象)。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语言学习者没有注意到这些强制性关注点,开口便意味着社会性的死亡——因为没有办法通过语言与其他人交换想法、协调行动。
第四章《语法中的社会认知》与第八章《语言如何训练思维》直接相关,后者更侧重于心理语言学,也许是与埃文斯教授早年学习心理学的经历有关,也呼应了语言文化相对论。举凡色彩、数字、方位、对形状还是材质的优先感知,都可以通过精巧的心理学设计,发掘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笔者以为,四、八两章是在回答“语言是什么?”的本体论基础上,在认识论上的分叉推进,前沿观点迭出,值得社会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和心理语言学工作者反复参考。特别是第四章的内容,与进化论这一社会科学的元理论密切相关:人之所以为人,乃是通过社群内部的交流协调,得以超越环境的制约,而语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就是人性本身。这就将语言学、人类学提到了社会科学的核心地位。当今世界的种种纷争,有多少是因为语言和思维的隔阂而起?我们更需要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携手,才能尊重、挽救和利用多样性,避免庸俗化的普遍性思维带来的戕害,消弭人类社会之间的误读。作者对于另两个分支历史语言学或语言考古(五、六、七章)和语言艺术(第九章)的重要探索,笔者在此不赘述,留给读者细读。
第三个问题是,田野语言学工作者如何看待这本书?
语言学被作为“硬科学”而被重新定义,一本真正回归语言本体的语言学的读物少之又少。Words of Wonder既有有趣的语言现象的描写,科学的语言学方法论,也在更高的层面,更宏大的叙事之下为我们解读了这些微观语言现象的内涵。从时间和空间跨度而言,Words of Wonder中埃文斯教授以其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视角为读者呈现了一部世界语言通史;在专业层面,本书呈现了一个语言学家对人类认知世界的解读,读者在了解语言现象的同时,也知道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如何解读这些现象。一门语言往往蕴含着一种世界观。习得一门特定语言,便意味习得这门语言“切分”世界的方式,形成新的思维习惯。
那些未被了解的语言或许蕴藏着解开人类谜题的钥匙,令人扼腕的是我们还不知道那些钥匙藏在哪里,而那些钥匙却不可避免地消失在时空之中。面对这样的现实,语言学家们能做的并不多,只有深入田野中去记录那些正在消失中的语言。本书的第十章的主题是濒危语言保护的重要性,紧扣联合国“2019国际本土语言年”的号召,展望语言学的学科的未来,作为一个以研究语言为志业的学科,对大量濒危语言的忽视确实令人扼腕。作者犀利地指出,以描述性研究为博士课题的博士生很难在理论主导的学术界找到立足之地。如今语言学界对理论模型追逐的兴趣远大于对于语言现象的探索,但是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才是推动语言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科技赋予了语言学田野调查前所未有的便捷与无与伦比的精准度,录像机、录音机、运动相机等等设备的使用让语言学田野调查看起来很酷,这些设备的使用也让一些当地语言的发音人感到开心,有些年龄大的人会误会这些录音录像能让他们上电视,会盛装打扮来录音。但如本书作者所说,设备的加持并没有减轻语言调查的工作量,反之要不停地学习新设备的使用技术,存储平台、软件的操作,而听声音记笔记的本事,以及挖掘语言现象的看家本领都是设备无法替代的。即使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AI能够对濒危语言进行记录分析,甚至冷门一点的方言就可以难倒AI。在田野语言学中不得不大写的“人”字,也许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去理解人类世界最精妙的发明——语言!
笔者在数年间参与了东南亚(如尼泊尔境内的Tsum, Ghale;不丹境内的Bumthang)、非洲(苏丹境内的Kufo;博茨瓦纳境内班图语Setswana)以及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Wardaman)调查项目。通过这些研究,笔者感到,局限于单一语言的研究,可以在单一的世界观中构建一种完整性,与人类学的整体性观照(wholistic approach)有殊途同归之妙。比如可以通过词缀与语法结构分析一个语言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或者通过语义分析该族群对色彩或者亲属关系的认知,而本书对语言类型学的把握将每种广泛运用或是濒临灭绝的语言提取出其中的“基因”,从而构建人类语言认知的“基因版图” 。对于语言研究者,只有将这个“版图”与单一语言研究比对,才能准确找到并拓展人类对语言认知的外延。
Words of Wonder是Dying Words的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作了不少改变,并增加了一章),令人欣慰的是如今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一词一宇宙》也已面世。洗练的文字,有趣的语言故事,以及更深层面上作者对历史、语言、文化的思考,让本书的读者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和人类学工作者,大学生甚至中学生也能在阅读中获益匪浅。这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笔者初次接触这本书是若干年前对语言学认识模糊的阶段,被其中有趣的语言现象启迪,开启了语言研究之路。2021年有幸参与本书再版的编校,再次细读本书的章节也有了醍醐灌顶之感。
这本书中文版的翻译更是值得称赞,就像江文瑜教授在中文版序言中写的,“将words of wonder 翻译成‘一词一宇宙’虽与英文原文略有不同,却能巧妙传达了本书的精髓,也让笔者想到《华严经》所说‘一花一宇宙,一叶一菩提(如来)’的境界”。
中国语言资源丰富,但我们却对其多样性知之甚少,是近几年来能最快发现“新”语言的地区之一。埃文斯教授也在书中多次提及南岛语壮阔的海洋迁徙以及多种语言汇聚碰撞下的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也写下了对华语读者的期许——“新一代华语圈语言学家展现出语言学这个领域的十足魅力……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去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希望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带着母语的觉知理解书中这些奇特的语言现象之后,能够对母语和世界上各种瑰奇的语言的认知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