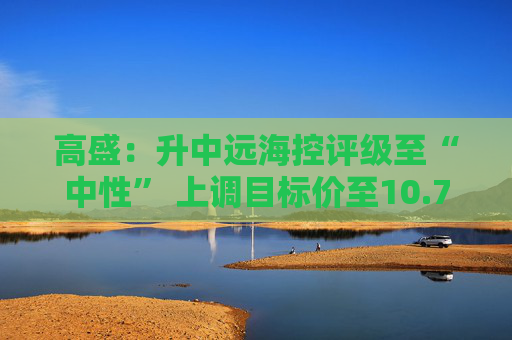洞天寻隐·罗浮纪丨苏远鸣:罗浮山宗教地理研究(七)洞天
- 每日科技
- 2024-09-21 09:05:24
- 25
第三章
洞天
从我们一开始研究罗浮山,在《指掌图记》的第一句话中,我们就知道这座山是一个洞天,在十大洞天中排行第七。
1. 十和三十六两个体系
沙畹在《投龙简》(Jet des dragons)的一章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497]。他的研究主要基于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杜光庭去世于919年之后不久,因此,“他的创作活动因此肯定是在9世纪或10世纪初[498]”。杜光庭这部著作中列举了五岳、十大洞天、五镇海渎、三十六靖庐、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灵化二十四,以及其他名山。需要注意的是,道教地理学中既有十大洞天体系也有三十六洞天体系。沙畹试图判断它们相对的年代,提出了以下观点:
在十大洞天的体系中,第八洞天是句曲,教内名为“金坛华阳天”[499]。陶弘景曾在492年前后隐居句曲,《梁书》编者引用了他所说的“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500] ”沙畹指出这段文字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早在大约500年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十大洞天体系。
他还注意到,在十大洞天体系中,“洞”和“天”两个词是分开的。比如我们所感兴趣的例子:罗浮洞、朱明耀真天(参见本章,2.)。相反在三十六洞天中,洞天两个词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衡山的朱陵洞天。沙畹认为“洞”这个词在《梁书》中是“洞宫”一词的缩写,意思是隐藏的或秘密的宫殿,归属于居住在特定天界的神仙。所以说,“洞天”是一个复合词组(composé hybride),仅此一点就可证明,三十六洞天的系统比十大洞天晚。
沙畹进一步指出,三十六洞天的地名与唐代使用的名称一致,而另一系统的地名则更古老。
最后,沙畹补充道,他所能找到的投龙仪式中涉及两大系统的地点几乎都属于三十六洞天体系。他也发现,这种仪式似乎在唐朝初期才开始出现。因此,他的结论是,十大洞天在6世纪早期就已经为人所知,而三十六洞天则似乎在7世纪才出现。
我们可以补充几点意见。沙畹忽略了一个文本,即陶弘景本人的《真诰》,根据该文本:“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坛华阳之天。[501]”《真诰》的本文很可能在后世被重新加工,但是这段话的真实性可以由另一部作品确证[502]。因此,三十六洞天体系似乎从5世纪末就为人所知。这些洞穴的教内名称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5世纪上半叶,罗浮山中洞穴的教内名称就被谢灵运引用,据他所说是从某本书上得到的信息(参见第二章,第三节,3.)。
大洞天体系的数字“十”在纯正的中国数字符号中没有特殊意涵。它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相反,数字三十六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具有宇宙论价值。它是九的倍数,代表了陆地上的上古九州,以及它们对应的九座山等等。那么,在三十六洞天系统之前,先出现了九大洞天系统的话,也不是不可能。事实上,我们在谢灵运的《罗浮山赋》中读到,“若乃茅公之说……洞四有九,此惟其七。”[503] 三十六是七十二的一半。七十二是福地的数目,这是道教中的另一系列圣地,也与洞天的列表相关。七十二和三十六都是三百六的子倍数,三百六是一年的天数的整数。因而这两个数字象征着天空和大地。人们就将天空想象成洞穴的拱顶,或者类似的,把天空想象成一口钟。洞穴的拱顶上倒挂着钟乳石,根据这种双重的意象,钟乳石被认识是钟或者天空的乳房(mamelle)。钟的乳房确实是以纽扣或者凸起的形式呈现在铜钟,排列在它们的侧面,共有三十六个,分为四部分,每部分有九个。另一方面,将土地划分为三十六块很常见,比如秦始皇曾将他的国土分为三十六郡。葛洪在他的《抱朴子》一书中谈到适合隐居和炼制不死之药的地点、山脉或岛屿时也列出了三十六个[504]。
与其认为十大洞天系统早于三十六洞天,不如承认原本有的是(由九洞天扩展而来的?)三十六洞天,然后再从中选取了前十个。这个观点来自《茅君内传》,遗憾的是,这段话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实:“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大者别有十山。[505]”这一假设也可以从杜光庭的论著那里得到佐证。他在第一份列表中明确描述了十大洞天,在第二份列表中只是简单地列出了三十六洞天,仿佛这是仅有的信息。后一份列表的构成也很奇怪。作者已经在之前的章节列出了“中国五岳”及其佐山。同样的山峰再次出现在三十六洞天的开头,让人们觉得他们好像是用来补充缺漏的。列表需要十座山,但是它们只有五座,幸好他们还有佐山凑数。一部类书提供了以下引文:“唐吴筠《天柱观记》:太史公称,太荒之内,名山五千,其在中国,有五岳作镇,罗浮、括苍辈十山为之佐命,其馀不可详载。[506]”同样的分类方法也可以在前文提到的杜光庭著作中的《中国五岳》标题下面找到:“东岳泰山,岳神天齐王,领仙官玉女九万人。山周回二千里,在兖州奉符县。罗浮山、括苍山为佐命,蒙山、东山为佐理。”总共有二十九座山,分布并不平衡:东部包括一座主山,搭配两座佐命山和两座佐理山,总共有五座山。南岳和中岳也是有五座,但是西岳有八座山,北部有六座山。辅佐的山峰似乎是附加的。根据前面杜光庭引用过的古老文本,以及太史公的论断,很可能只有十座佐山,每两座拥有一个共同的岳山。杜光庭还引用了不为人知的《龟山玉经》[507]。杜光庭的列表是最早的包含佐山的五岳列表[508],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在5世纪的《神仙传》中看到泰山的两个佐山:“王方平常治昆仑山,往来罗浮山括苍山。[509]”
需要指出的是,这句话提到的罗浮并不在广东,而是位于浙江温州地区。它也许就是位于太湖之南的罗浮山,又名浮玉山(参见第二章,第三节,4.)。但是广州罗浮山的名声很快就盖过了它。在从五岳的佐山向十大洞天之一转换的过程中,罗浮这个山名从浙江转移到了广东。
这几个反思并没有解决这两种道教圣地系统哪个更古老的问题。我们只是稍微在时间上追溯了一下这些分类的来源,特别是与罗浮山相关的内容。
2. 洞天的属性
在“洞天”这个词语中,“洞”字确实如沙畹所说,有“秘密、隐藏”的含义,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洞穴”。“洞穴”或者“洞宫”在本质上是一个地下空间,通过隧道与其他地下空间连通。我们已经提到的洞庭就是最好且最古老的例证。晋代的一篇文献解释了它的结构:“阳羡县东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潜行地中,云无所不通,谓之洞庭地脉。[510]” 最著名的结构是这样的:“洞庭山有宫五门,东通林屋,西达峨眉,南接罗浮,北连岱岳。[511]”这里只提到了四个门,第五个门是中门,可能是连接宫殿与外部[512]。
在描述“洞天”中的“天”这个词时,沙畹最先强调了一些圣地中“天界”的属性。洞天是一个“隐藏的天堂”。《真诰》讲述了一个道士探访洞庭洞穴的游历:“汉建安(196-220)之中,左元放闻传者云:江东有此神山,故度江寻之,遂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门,入洞虚,造阴宫,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种。元放周旋洞宫之内经年,宫室结构,方圆整肃,甚惋惧也。不图天下复有如此之异乎?[513]”
左元放进入山洞之后,就跨越了人间与仙界的界线。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很长时间做准备。他一到这里就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小屋,就像隐士们在山上所做的那样,他称之为“阴宫”,意思是墓穴之外的宫殿。他搜集了草药,这些草药是三茅君授予他的,所以都是最神异的。可以说,洞天是整座山的精髓。进入其中就可以搜集草药,制作不死之药,“住”和“游”通常都是危险的事情。《抱朴子》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章节中提到了那些未做准备就入山的人所面临的危险,并且教授了人们应该怎么做:选择一个合适的日期,斋戒七天[514]。进山就像进洞一样,是一种宗教实践与皈依。
洞天是世外天界的最好证据就是普通人看不到它。在谈到句曲洞天时,《真诰》说,“虚空之内,皆有石阶,曲出以承门口,令得往来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觉是洞天之中,故自谓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异,草木水泽,又与外无别。飞鸟交横,风云蓊郁,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谓洞天神宫,灵妙无方,不可得而议,不可得而罔也。[515]”
这种有关洞天不可进入性的形而上学观念并不普遍。可能更多的人认为,“此洞深隐不露,行人过之不知有洞[516]”。但是无论是不可进入还是不可发现,洞天都是一个“隐蔽的天界”。
不过,“天”的首要含义当然是具象的“天”。在这个意义上,洞天是“以洞的形式存在的天,洞的天,或者说是在洞中的天”。这些洞穴最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它们含有天空。在解释了句曲的洞穴金坛华阳天是一个真正的洞穴(“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并且在描述其尺寸之后,《真诰》继续说道:“其内有阴晖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内,明并日月矣。阴晖主夜,日精主昼,形如日月之圆,飞在玄空之中。[517]”高似孙(13世纪)[518]的注释补充道:洞穴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被比喻为“小天”,以区分于星斗所对应的“大天”,尽管它们与后者相类似,并以同样的方式升起和落下,但是它们不应该被混淆。而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这是很容易混淆的。
洞穴中的天空这一概念在我们看来可能非常奇怪,但是它有古老的渊源。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讨论过的内容(见本章,1.):洞穴的拱顶及其“乳头”是天穹的替代(substitut)或象征(figuration)[519]。
3. 罗浮山中的洞天
罗浮山中的洞天正是《指掌图记》(见第一章,1.)中提到的朱明洞。它位于冲虚观的后面,正好在朝斗坛的北边。那里并没有真实的洞穴,只是一片荒野之地。苏东坡曾经去过那里,他说:“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锵鸣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520]”
宋朝时,人们在此树立了一块石碑,刻有“朱明耀真”的字样,这在道教文化体系中确实是洞天的名称。杜光庭作品中的“十大洞天”包含:“第七,罗浮洞朱明曜真天,广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罗县属修州。[521]”但是它的名字早在杜光庭之前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发现它已经出现在年代无法确定的《茅君内传》[522],以及逝世于433年的谢灵运的《罗浮山赋》[523]。
虽然这个洞穴极其隐蔽,但还是有人参访过。唐天宝初年(742-756),道士申太芝奉命祭山,他表示想要参观朱明洞。一位热衷古迹的地方官员发现了洞穴的入口:“以藤担笼,垂一人下洞,约五丈余,却出。曰:下视无底,日月星辰无不备焉,初有白云,须臾散漫五色。[524]”
罗浮山洞天的名字一直备受猜测,以下是一些主要观点:“朱明言向南也,罗浮诸洞不皆向南,惟兹洞负北面南,南阳名方也,其色赤其卦离,故曰朱明。且四方之有南,即四时之有夏。《尔雅》谓‘夏为朱明[525]’,《史迁》乐书谓‘夏歌朱明[526]’,《汉书》郊祀章有‘朱明盛长之’辞[527],则洞以方向名,朱明也。[528]”这些都可以作为对洞穴名字的解释。
下面的引文则是关于洞穴本身性质的理论:
朱明洞为一山之根本,譬之人身之脐,精神所穴[529],日月归宿其中,故曰洞天。
临菑有天齐,当天中,斯洞其亦天齐乎?[530]曰朱明者,言纯阳无阴也。盖天好阴,地好阳,洞中而有天,乃阴含阳,太极未分之象也。朱明洞群峰如环,中虚以成奥室,于卦为离,离为日,故曰朱明之洞。曰为天之主,洞而有日,天之精神在焉,故曰洞天。天数七,第七洞天,又天之所都也。又凡地皆虚,惟虚,故多其窍穴以为洞府。其曰朱明耀真者,言南粤为大火地,其洞府皆火之所从出,朱明耀真乃天下之火府也。水府实而火府虚,故与五岳相通,而玉笥之山[531]有八窍,南窍为罗浮,而勾漏、句曲洞天[532],亦南通罗浮,皆大道。又罗浮在东,西樵在西,彼此相望,日生于东,故罗浮为朱明耀真之天。其曰第七洞天者,七为火之成数,日复于七,罗浮为日之奥府,故为第七洞天也。凡地中之虚,皆天也。《记》曰:‘地载[533]神气。’神气者,天也,天以地而载,神气出于地中,实出于天中也。仙家所称洞天,皆在地中。仙人出入于洞天之中,盖出入于神气之中也。罗浮者,洞天之大者也,其小者凡山之虚处皆然,以其洞,故有天之名。洞者,虚也。山即地也,《易》言‘天在山中’。盖天不在天中,而在地中也。[534]
4. 罗浮山中的福地
在道教圣地的等级体系中,罗浮山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那就是它既有洞天又有福地。后者等级较低,这一点从它们的数量和名称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它的数量是七十二个,是洞天数量的两倍,其次它们被称为“地”,地低于天[535]。罗浮山的福地是泉源山(见第一章,1.),它是第三十四福地,由华子期掌管。[536]
5. 罗浮山与其他山的关系
作为洞天的罗浮与其他名山的洞天在地下有连通。我们已经知道,洞庭的洞穴南门有通往罗浮的隧道,尽管这可能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罗浮山,不过理论上来说,这条隧道确实应该是通往朱明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罗汉岩中有一个地下通道通往句曲(参考第一章,1.)。古籍中没有具体的说明,只提到在罗浮山“山有洞通句曲”[537]。罗浮山以同样的方式与其他非常遥远的山峰连通,特别是与四川的峨眉山。11世纪的一个文人写道:“其岫穴所通,远则峨眉,近则金坛。[538]” 这个连通很可能与“蛇穴”有关。至于罗浮山与南岳衡山的地下连通则不那么令人惊讶:“南岳君也,罗浮其东诸侯也。罗浮分南岳之司,以治五岭,而朱明洞与南岳之朱陵洞相通。”[539] 还有其他不太重要的连通,比如金华山(浙江,第三十五洞天),据说它与“罗浮之豚”有关[540]。我们在上面看到(第三章,3.),它也被归为勾漏山,甚至与五岳有关。一个纯粹地域性的关系是罗浮山与广州西部的浮邱山之间的关系,它们通过广州北部的白云山连接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浮邱山上有一座寺庙叫朱明观,因为这座山是通往罗浮山的朱明洞的门户[541]。
——————————
注释:
[497]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t. III, 1919, p. 131-168.
[498] Wieger, Canon taoïste. n°594. 译按:《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499] 参见第一章,1.
[500] 《梁书》,卷51,5b-6a(相关段落:5b),沙畹误引《南史》,该书有相同的传记(卷76,4b-6b,相关段落:5a)
[501] 《真诰》,(Wieger, Taoist Canon, n°1004),卷11,5b-6a。沙畹知道这个文本,并在一个注释中引用了它(第131页,n°1),但他指出,这里的第八洞天是在三十六洞天中,而在杜光庭的经典中,它不在三十六洞天,而是在十大洞天中,编号同样是第八,这在他看来是需要怀疑的。然后他指出,现在的《真诰》可以追溯到1223年的版本,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被重新加工的。这的确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完全准确。
[502] 山谦之,《南徐州记》(六朝宋的作品,被收录于《隋书》,卷33,10a)也说,“洞天三十六所,句曲为第八”(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九,7a)。陶弘景的另一部作品《登真隐诀》(Wieger, Taoiste Canon, n°418),提到了赤城山的洞穴,这是三十六小洞天之一。(《太平寰宇记》,卷89,10b)。这个洞穴也被杜光庭列为十大洞天之一(第六洞天)。
[503] LFHP,卷14,1a。茅君无疑是茅盈,《隋书》(卷33,9a)收录了他的仙传,题名为《太元真人东乡司命茅君内传》,一卷,由其弟子李遵撰写。在其他文本中也被题名为《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作者为李道(比如《云笈七签》,卷104),抄录在几部类书中时都被题名为《茅君内传》。最早的引文来自《艺文类聚》(卷7,29ab,1879):“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罗浮山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
[504] 《抱朴子·内篇》卷4,41b-42a。他实际上只列出了34个圣地,因为其中两个名字是用来描述其他地点的。
[505] 《唐宋白孔六帖》,引用自LFHP,卷8,1b。 十大洞天是按照杜光庭的论述中的顺序和名称进行的列举和编号,但是它完全是延续的《真诰》提供的信息。校按:《唐宋白孔六帖》原文未见“其大者别有十山”7字,当为《会编》所添。
[506] 《唐吴筠天柱观记》,出自《玉海》,卷21,29b。同一段落还被引用在杜光庭的序言中(《全唐文》,卷932,4b),但是省略了《玉海》引文中的两座山。
[507] 《龟山玉经》,在书目中没有列出。
[508] 校按:五岳佐命十山应出自汉末魏晋之际道书《五岳真形图》当中。至迟于梁陶弘景所编《陶公传授仪》之“授受五岳图法”中已明确见有五岳与佐命十山记载了。参见:王卡.敦煌残抄本陶公传授仪校读记[J].敦煌学辑刊,2002(1):95.
[509] 《神仙传》,卷2。
[510] [晋]周处,《风土记》,《北堂书钞》,卷158,3a。
[511] 《述异记》(5世纪),卷上,15a,(《汉魏丛书》)。
[512] 《真诰》(卷11,7a,《道藏》版)也说,“句曲之洞宫有五门,南两便门,东西便门,北大便门,凡合五便门也……句曲洞天,东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罗浮,皆大道也。其间有小径杂路,阡陌抄会,非一处也。”我们已经在上文(第80页,n.2)提到了洞庭与太湖或句曲之间的混淆。
[513] 《真诰》,卷11,7a-b,关于左元放,即左慈,参考《神仙传》卷5。
[514] 《抱朴子内篇》,卷17,1b
[515] 《真诰》,卷11,7a
[516] 关于这一主题的例子,比如罗浮山的“小蓬莱洞”。《浮山纪胜》,《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462a。
[517] 《真诰》卷11,6a-b。译按:高似孙注释:按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小不同,盖犹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昼夜,便有出没,亦当与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崖畔,了不得穷,此小天边际,殆可扪睹。日月出入,则应有限。当是忽然起灭,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
[518] 校按:高似孙(1158-1231)仅为宋刊本《真诰》序的作者,《真诰》注为陶弘景作。
[519] 根据M. Granet, La pensée chinoise, p. 346.
[520] 苏东坡,《游罗浮题记名记》,LFHP,卷11,4a.
[521]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Wieger, Canon Taoïste, n°594)p.4a。《云笈七签》中另外一个版本的论述(《四部丛刊》版,卷27,3a)“在循州博罗县,属青精先生治之。”循州在唐代时期位于惠州,但是杜光庭笔下的修州从未真实存在,所以可能是循州的误称。
[522] 《太平御览》,卷41,7a,特别是《艺文类聚》,卷七,29a-b。
[523] LFHP,卷14,1a-b。
[524] 《唐宋白孔六帖》,卷5,28a,申太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里提到了唐代对于这座山的祭祀(参见第五章,4.)。他的传记见于一部未注明日期的道藏中的文本(Wieger, Canon Taoïste, n°448,译按:《云阜山申仙翁传》),虽然这里没有提到罗浮山,但是肯定是同一个人,他在其他地方被称为申元之或者申天师(参见Wieger,Canon taoïste,n.293,译按:《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9,6b-7a,以及H. Maspero, “Les procédés de « Nourrir le Principe Vital » dans la religion taoïstes ancienne”, JA, 1937,第236-237页。)
[525] 《尔雅》,释天,2b 。(《蜀南阁》版,1884)
[526] Chavann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t. III, p. 236。
[527] 《前汉书》卷22,18a,百衲本,这是一段引文,因为《汉书》中的这段话与《诗经》中的相同,不同的是它给出了诗歌的文本。这是由沙畹翻译的(同上,appendice 1, p.615)
[528] LFHP,卷2,1b-2a.
[529] 参见H. Maspero, JA, 1937. p. 198.
[530] 临菑在山东,天齐是一个有五个开口的泉眼或者洞穴。它就像天的肚脐,它面向天空的中央,这无疑就是被人们称之为“井”的天齐的星斗(参考G.Schlegel, Uranographie Chinoise, p.408)。这个地方是八神的首位“天主”的祭祀场所(《史记》卷28,4b,文本与注释;《读史方舆纪要》卷35,11b )。有趣的是,《广东新语》的作者两次将洞穴比作肚脐。也有人将洞穴比作腧穴:“罗浮之洞,周回五百里,盖举其全犹人之一身也,以朱明洞为在冲虚,后者犹人之有腧穴也”(《浮山纪胜》,《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461a,引用先泰泉黄佐的观点)。这也印证了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之间的对应。
[531] 这是会稽山区的一部分,是通天之柱。译按:玉笥山,位于江西省峡江县,为第十七洞天、第八福地。八窍,即洞天八门。按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七“玉峰子”条载:“(玉笥山)其下有八窍,南窍惟罗浮、勾漏,其东窍惟武夷、金华诸山,西之北曰庐阜、曰大小酉,北之西曰太白、青城,八窍各为一宫,镇于四维,惟玉笥居中。” 又《玉笥实录》序载:“其山洞穴通连黄屋、桃源、罗浮、南岳、苍梧、武夷、天台、空峒、西城、勾曲金坛之洞府,盖以洞天有八卦门。”
[532] 广西勾漏山
[533] 指的是“天覆地载”。参见注319。
[534] 《广东新语》,卷3,27b-28a
[535] 洞天与福地两者是对立的,也是有差等的,因为天与地对应,并且高于地,这就是为什么福地的数量是洞天的两倍。
[536] 《云笈七签》,《四部丛刊》版,卷27,14a。杜光庭的文本中并没有关于罗浮山是福地的说法。邹师正则认为福地的掌管者是子华(参考第一章,1.)。这可能是混淆了两位仙真的名字,因为第一个和第二个的子字相同。
[537] 《南越志》,《太平御览》,卷41,7a
[538] 余靖,《陈宫师题罗浮山诗序》,LFHP,卷10,15a
[539] 《广东新语》,卷3,4b。湛甘泉于西樵隐居之左,开小朱明洞门以寓意罗浮,于右开朱陵门以寓意衡岳,言其二洞相通也。(LFHP,卷9,10a)
[540] 《金华赤松山志》,4a,(Wieger, Canon Taoïste, n°596)
[541] 朱明门户,参见《广东新语》,卷五,4a。地下是从浮碇开始的,在山的东部。浮丘,朱明洞的门,也是白云山的门。同样我们也说罗浮是洞庭的门户。(《粤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203a)。关于浮邱,参见第二章,第三节,1. 校按:原文“(浮丘)有馆曰朱明……盖以浮丘在罗浮之西,为朱明门户。”

苏远鸣(Michel Soymié,1924—2002),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宗教与文献,涉及民间宝卷、佛道关系等主题,尤其在整理伯希和所藏敦煌文献方面贡献巨大。

张琬容,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远东研究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集中于道教与民间信仰,法国汉学史。